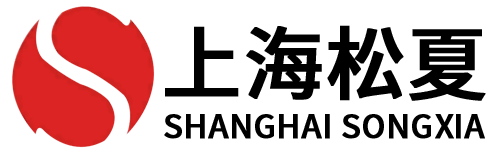汕優(yōu)63水稻是哪發(fā)明的,汕優(yōu)63稻種

人們介紹他的時(shí)候,常用這樣一句話:很多中國(guó)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,但是,很多中國(guó)人都吃過(guò)他的米。
文|賴祐萱
編輯|沈時(shí)
阿輝
真是糟糕,這樣的天氣。
離福建省尤溪縣西城鎮(zhèn)麻洋村還有10公里的時(shí)候,謝華安開(kāi)始緊張了。這位福建省農(nóng)業(yè)科學(xué)院的水稻育種家不停摩挲著那雙磨砂紙般的雙手。今天他要到麻洋村去看阿輝的稻田。
福建連日高溫?zé)o雨。正是水稻即將抽穗結(jié)實(shí)的時(shí)候——也正是它們脆弱敏感的時(shí)候。他很擔(dān)心它們。高溫會(huì)使稻葉水分大量蒸騰,葉片因缺水而枯萎;如果又沒(méi)有控制灌溉的水量,過(guò)多的水分會(huì)導(dǎo)致根系缺氧受損,引發(fā)葉片發(fā)紅。
三明市尤溪縣西城鎮(zhèn)麻洋村有一片重要的試驗(yàn)田。2000年,時(shí)任福建省農(nóng)業(yè)科學(xué)院院長(zhǎng)的謝華安在麻洋村認(rèn)識(shí)了村里的阿輝。那時(shí)阿輝剛過(guò)而立之年,他是遠(yuǎn)近聞名的種糧好手,同樣的田,同樣的種子,他總能比別人種得好。自那時(shí)起,謝華安就把一片重要的試驗(yàn)田交給他打理。如今,阿輝已經(jīng)五十多了,謝華安也已年屆八十。
拐過(guò)村口,要上一段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斜坡。車子爬上坡道,阿輝的百畝稻田出現(xiàn)在眼前。夕陽(yáng)打下來(lái),淡黃的光暈覆上一片綠色。
阿輝!
車子還沒(méi)有停穩(wěn),謝華安就開(kāi)始喊。阿輝從屋子里跑出來(lái),戴著草帽,趿著拖鞋,穿著麻灰色的襯衫,眼睛笑成一道縫。
謝華安遞過(guò)一支煙。哎呀,我可是擔(dān)心壞了。他聲音洪亮,像孩子一樣開(kāi)心,我都不敢來(lái),怕是紅紅一片哦。現(xiàn)在好了,阿輝,今晚我可以睡個(gè)好覺(jué)了。
寒暄完,照例是下田看稻子。已過(guò)50歲的阿輝攙著80歲的謝華安走上田埂。阿輝家的田埂有小小的臺(tái)階,他特意砌的,這樣謝華安每次來(lái),會(huì)好走些。他們撥開(kāi)稻子仔細(xì)地看葉片和穗子,說(shuō)著今年的稻子有什么不同。
過(guò)去20年里,隔段日子謝華安就會(huì)來(lái)看看阿輝和他的稻田,最多一年能來(lái)上五六趟。20年間,阿輝的孩子們,老謝眼里的小不點(diǎn)兒一個(gè)個(gè)都長(zhǎng)大了,去省外上了大學(xué),但他們倆似乎都還沒(méi)變:一起下田看稻子,休息時(shí)一起坐在阿輝家的院子里——冬天曬太陽(yáng),夏天望著對(duì)面長(zhǎng)滿松木的山林。阿輝覺(jué)得謝華安也沒(méi)有變老,和他在一起,自己都感到更年輕了一些,而且,老謝講的什么東西,都很好玩。
阿輝私底下叫謝華安老謝,但在外人面前會(huì)驕傲地叫他謝院士。
這位謝院士在農(nóng)民心中曾經(jīng)是明星一樣的存在。人們介紹他的時(shí)候,常用這樣一句話:很多中國(guó)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,但是,很多中國(guó)人都吃過(guò)他的米。謝華安1981年培育成功并于1986年審定通過(guò)、1987年大面積推廣的汕優(yōu)63是中國(guó)乃至世界稻作史上種植面積最大的雜交水稻品種。少年時(shí),阿輝跟著父親也種過(guò)汕優(yōu)63,他記得這個(gè)品種好種到村里人都忘記了稻瘟病曾經(jīng)存在過(guò)——1970年代是雜交水稻在中國(guó)大力推廣的時(shí)期,也是稻瘟病盛行的時(shí)期,而抗病性強(qiáng)正是汕優(yōu)63的優(yōu)勢(shì)。
做小孩子的時(shí)候就跟著家里老頭子種田的阿輝從他結(jié)交的育種家那里學(xué)會(huì)了科學(xué)種田。他覺(jué)得種田不是開(kāi)玩笑,是非常認(rèn)真的事情。阿輝說(shuō),從植株之間的距離、溝渠的數(shù)量到施肥的日期,謝華安一點(diǎn)一點(diǎn)教他。這20年里,他在謝華安的幫助下,兩次打破再生稻再生季單產(chǎn)世界紀(jì)錄,他的小房子也被村民們戲稱為世界冠軍的家。
阿輝家門(mén)前 攝影 | 賴祐萱
饑餓與藝術(shù)家
謝華安對(duì)阿輝的世界并不陌生——不只是因?yàn)樗麄児餐P(guān)心的水稻。他1941年出生于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(qū)保豐村一座名叫三美樓的客家土樓里,父母也是農(nóng)民,離家到農(nóng)校念書(shū)之前,他做過(guò)最多的事情就是幫父母干農(nóng)活。村子也在山里,四周環(huán)繞著二三十座山,連綿不絕。小時(shí)候,謝華安站在三美樓的天井往上瞧,白云被困在四四方方的屋檐中間,他感到自己好像也被困住了——山外還是山,走出土樓似乎是一件很難的事。
兒時(shí)最深刻的記憶是肚子餓,餓怕了。每年眼巴巴地盼著的是幾個(gè)日子:過(guò)年,有白米飯和年糕吃;正月十五,有爆米花吃;端午節(jié),有粽子吃;八月十五,有月餅吃;立夏,有面條吃——立夏這天,保豐的客家人有個(gè)傳統(tǒng),再窮再不濟(jì)的家庭都要想辦法弄來(lái)一些面粉,給孩子們做一點(diǎn)面條吃。還有正月初二到外婆家,外婆一定會(huì)煮兩個(gè)雞蛋給他。一年吃幾碗米飯、幾個(gè)蛋,都是記得牢牢、算得出來(lái)的。剩下的日子,只有雜糧和稀飯勉強(qiáng)度日。
時(shí)過(guò)境遷,所有的記憶歸為一句話:沒(méi)有餓過(guò)的人根本不理解那一碗飯多大的價(jià)值。講起一些傷心的事,想起來(lái)毛孔都要豎起來(lái)。80歲的謝華安坐在棕色沙發(fā)上,聲調(diào)沉了下去;點(diǎn)了一支煙,停頓了幾秒,才繼續(xù)說(shuō)下去。
荒年沒(méi)吃的,祖母餓到最后都不會(huì)站了。謝華安記憶中祖母最后的樣子,就是她倚坐在家中的門(mén)檻上喊,我不甘愿啊,我就這樣餓死掉。外婆的最后一天也是躺在床上喊餓,央求舅舅找一碗稀飯,我吃了這碗稀飯我死了也甘愿啊。但是,荒年哪里去弄一碗稀飯給她吃啊。
他不會(huì)想到,后來(lái)解決人們的吃飯問(wèn)題成了他的職業(yè)。先是在15歲的時(shí)候,因?yàn)榧依锕┎黄鹚^續(xù)讀高中,讀了學(xué)費(fèi)和生活費(fèi)全免的農(nóng)校。畢業(yè)后,他輾轉(zhuǎn)幾所農(nóng)校當(dāng)了十三年老師;后來(lái)一個(gè)偶然的機(jī)會(huì),被調(diào)往三明市農(nóng)業(yè)科學(xué)研究所工作,開(kāi)始雜交水稻育種的研究。
在謝華安的故事里,到離家40公里的農(nóng)校念書(shū)或許可以被視作一個(gè)分界,現(xiàn)實(shí)與浪漫之間的分界——借用一下,美國(guó)人文地理學(xué)者段義孚在《浪漫地理學(xué):追尋崇高景觀》一書(shū)中的浪漫概念,段義孚認(rèn)為浪漫的核心是求索——就像尋找圣杯的壯舉一樣,浪漫的人尋求冒險(xiǎn),甚至是追尋那些他們無(wú)法闡明的更為神秘的事物。簡(jiǎn)單地說(shuō),浪漫是一個(gè)與日常生活相對(duì)的概念,從本質(zhì)上來(lái)說(shuō)是對(duì)日常生活的超越,這里面混合了人類完美主義的信仰,對(duì)能量的敬仰……對(duì)于人類的偉岸與卑微、強(qiáng)大與悲苦之矛盾的認(rèn)知。
在離開(kāi)家到農(nóng)校念書(shū)之前,日常生活在謝華安的世界里占主導(dǎo)。盡管對(duì)一個(gè)孩童來(lái)說(shuō),好奇心總是難免的——他想到村邊上山匪聚集的森林里探險(xiǎn),也想了解土樓三面環(huán)繞的田野里藏著的秘密(比如,為什么蟲(chóng)子會(huì)讓水稻生病?)——但吃飽終究是最重要的事,至于更高的理想,成為科學(xué)家什么的,都是太遙遠(yuǎn)、完全不曾想過(guò)的事情。
到了農(nóng)校,一個(gè)新的世界展開(kāi)在他面前。在這里,糧食不再承擔(dān)一個(gè)家庭具體的吃飯問(wèn)題,他第一次在吃物中看到了超出吃本身的東西。他發(fā)現(xiàn),原先被稱作水稻、地瓜、花生的作物被老師們叫作材料,而每個(gè)材料都有屬于自己的編號(hào)和名字。它們成了一個(gè)個(gè)獨(dú)立的、有面孔的個(gè)體,他每次在田間找它們,都覺(jué)得像在找一個(gè)朋友:誒,XXX,你今天怎么樣?他從此迷上了試驗(yàn)田。
后來(lái),每一株植物都是一個(gè)活生生的個(gè)體——這成為愈發(fā)深刻的感受。在向我解釋育種的技術(shù)細(xì)節(jié)的時(shí)候,謝華安用孩子打了比方。水稻就像一個(gè)小孩子。有的比較漂亮,有的適合運(yùn)動(dòng);有的個(gè)子高,有的個(gè)子矮;有的膚色白,有的紅潤(rùn);有的性情溫和,有的暴躁;有的節(jié)奏感強(qiáng),有的善于動(dòng)手。哪一個(gè)孩子是最好的?只能等他長(zhǎng)大,等到最后再來(lái)評(píng)價(jià)他。水稻也是和人一樣,有自己的性格,會(huì)變化,會(huì)生長(zhǎng)。
區(qū)別只是在于,人類給自身的生育繁衍設(shè)置了嚴(yán)格的禁區(qū),孩子的生長(zhǎng)主要是靠自然本身完成,但水稻本就是人類馴化的作物,因此從種子開(kāi)始就有人類的操控。育種可以理解為人類與自然的共同創(chuàng)作。一株水稻能吸收到的能量是有限的,謝華安們的工作就是將這有限的能量進(jìn)行合理的分配。水稻有四個(gè)主要的性狀維度——豐產(chǎn)性、優(yōu)質(zhì)性、抗性和廣適應(yīng)性,通俗的說(shuō),它們對(duì)應(yīng)了人類需要水稻實(shí)現(xiàn)的四個(gè)主要目標(biāo),就是產(chǎn)量高,口感好,抗病蟲(chóng)害,能適應(yīng)不同的環(huán)境,育種家們需要平衡這四個(gè)相互沖突的目標(biāo)。
育種難就難在像藝術(shù)家一樣,所有的能量能夠合理地分配,給抗性一點(diǎn),給豐產(chǎn)性一點(diǎn)。謝華安說(shuō)。汕優(yōu)63的成功就是在豐產(chǎn)性、抗性和優(yōu)質(zhì)性上取得了相對(duì)理想的平衡,它在保證雜交稻豐產(chǎn)的前提下,解決了此前雜交稻一直沒(méi)有得到解決的抗病性差的問(wèn)題。
謝華安自己也培育過(guò)抗病性差的雜交稻品種。1975年,他培育的一個(gè)雜交組合在福建試種時(shí)表現(xiàn)良好,豐產(chǎn)優(yōu)質(zhì),但第二年在海南英州大面積試種時(shí),秧苗染上了稻瘟病。謝華安記得,當(dāng)時(shí)有個(gè)農(nóng)民哭著對(duì)他說(shuō),11畝多農(nóng)田收獲的谷子連三只母雞都喂不飽。不抗病的雜交水稻,我當(dāng)時(shí)感到肯定沒(méi)有前途了。謝華安向我回憶,選育出抗病的雜交稻成為他后來(lái)最重要的目標(biāo)。
雜交水稻的性狀是由父本與母本決定的,想要培育一株抗性強(qiáng)的雜交稻,就要先找到強(qiáng)抗病的親本。1978年春天,謝華安將圭630選為父本,IR30為母本,開(kāi)始進(jìn)行選育。圭630是謝華安從一個(gè)圭亞那華僑那里得到的,它的特點(diǎn)是粒大,恢復(fù)基因強(qiáng),且不感光——這正彌補(bǔ)了IR30的缺陷。IR30抗稻瘟病和白葉枯病,株葉形態(tài)好,具有強(qiáng)恢復(fù)基因,但雜交后代都是感光型水稻(編者注:所謂感光,也就是作物對(duì)光照、溫度都很敏感,晚稻品種9月末才會(huì)抽穗,溫度如果低了減產(chǎn)風(fēng)險(xiǎn)很大)。
謝華安采用了當(dāng)時(shí)國(guó)際上有育種家使用的一種叫做旱病圃的抗病性試驗(yàn)法,這是一種人為制造惡劣發(fā)病環(huán)境,對(duì)水稻進(jìn)行病毒圍攻的研究方法。他將圭630和IR30雜交組合的F1代種植在福建省稻瘟病最重的五個(gè)縣,再?gòu)奈鍌€(gè)縣中選擇稻瘟病最重的幾個(gè)鄉(xiāng),最終在幾個(gè)鄉(xiāng)里選擇最重的幾片稻田。每一年,同一份材料種植在海南和福建四地的9片稻田,然后從這些材料中選擇抗病表現(xiàn)好的,再進(jìn)行下一代的種植。為了增強(qiáng)毒效,他還將稻瘟病發(fā)作的水稻葉片摘下來(lái),切碎、泡水,然后將浸潤(rùn)過(guò)病葉的水往試驗(yàn)田里噴灑。
1981年,謝華安終于選育出一株抗病性極強(qiáng)的恢復(fù)系水稻品種明恢63。明恢63抗住了所有的病菌誘發(fā)測(cè)試,大穗大粒,稻葉厚實(shí)而挺拔。謝華安又將珍汕97A與明恢63進(jìn)行配組,獲得了新組合汕優(yōu)63。珍汕97A是另一位重要的水稻育種家——顏龍安院士培育的第一代雜交水稻不育系,它生育期短,適應(yīng)性好,但不抗病。1986年,在經(jīng)過(guò)五年的制種技術(shù)研究、南方稻區(qū)試驗(yàn)、中晚稻區(qū)試驗(yàn)后,汕優(yōu)63通過(guò)福建省審定,于次年開(kāi)始在全國(guó)大面積推廣。
汕優(yōu)63水稻 受訪者供圖
候鳥(niǎo)
1986年全國(guó)雜交水稻顧問(wèn)組專家會(huì)議在福建召開(kāi),袁隆平和謝華安說(shuō):老謝,祝賀你。你的『汕優(yōu)63』是全國(guó)最大面積的水稻品種了。
謝華安從此有了代表作。1980年代末,汕優(yōu)63從海南三亞的南繁基地一直延綿至山東東營(yíng)的勝利油田。一位出身農(nóng)村的農(nóng)學(xué)博士說(shuō),當(dāng)年他老家的農(nóng)戶們?nèi)シN子站買(mǎi)雜交稻種,根本不用說(shuō)出品種名字,一句話,買(mǎi)種子咧,老板遞過(guò)來(lái)的肯定就是汕優(yōu)63。在很長(zhǎng)一段時(shí)間里,汕優(yōu)63就是水稻的代名詞。
謝華安的水稻育種生涯是從1972年開(kāi)始的。這年春天,國(guó)務(wù)院作出成立全國(guó)雜交水稻協(xié)作攻關(guān)組的決定,從各個(gè)省(市、自治區(qū))抽調(diào)年輕的農(nóng)科技術(shù)員前往海南南繁育種基地,進(jìn)行雜交水稻的育種工作。謝華安就是被抽調(diào)的眾多年輕人之一。汕優(yōu)63就是這一時(shí)期的產(chǎn)物。
對(duì)謝華安來(lái)說(shuō),那是一場(chǎng)持續(xù)十幾年的盛大的水稻藝術(shù)節(jié)。每年有成千上萬(wàn)的作物育種家、遺傳學(xué)家、生物學(xué)家、植物病毒學(xué)家聚集在南繁基地,交流、切磋關(guān)于水稻、關(guān)于育種的一切。這個(gè)是現(xiàn)代人哪里能想象的?謝華安回憶南繁往事時(shí)向我感嘆。截至70年代末,參與南繁藝術(shù)節(jié)的科研人員超過(guò)20萬(wàn)人次,涉及29個(gè)省的400多家單位。被譽(yù)為雜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,第一個(gè)讓野敗出穗、成功培育不育系雜交水稻的顏龍安,第一個(gè)選育出強(qiáng)恢復(fù)系水稻、實(shí)現(xiàn)了三系配套的張先程,提出中國(guó)獨(dú)創(chuàng)的雜交水稻兩系法的石明松,創(chuàng)造新型不育系紅蓮品種的朱英國(guó)——中國(guó)雜交水稻發(fā)展史上重要的名字都在那里生活過(guò)。
謝華安現(xiàn)在回憶起那段時(shí)光,清苦,但也實(shí)在是快樂(lè)。
全國(guó)的農(nóng)學(xué)家一下涌到了一個(gè)原本人煙稀少的寂寥之地。一根蠟燭,一支鉛筆,做飯用的油和調(diào)味料,謝華安都要從福建的家里背過(guò)去。真的像走出原始社會(huì)才不幾年。謝華安回憶,做飯就是在房間的窗戶下砌一個(gè)灶,下雨的時(shí)候,幾個(gè)人拿著斗笠一層層地遮住。
現(xiàn)在想起當(dāng)初都好笑,謝華安說(shuō)起這些哈哈大笑起來(lái),那個(gè)真的非常艱苦。沒(méi)有房子住,就睡到倉(cāng)庫(kù)里,屋里有拖拉機(jī)、柴油和生產(chǎn)隊(duì)的種子、化肥、農(nóng)藥,所有的東西都?xì)w置到一個(gè)角落,剩下的地方打一個(gè)九個(gè)人一起睡的大通鋪。氣味刺鼻,但也只能將就睡。后來(lái)房東心疼他們,把房間讓給這些遠(yuǎn)道而來(lái)的科研人員,自己睡在廚房。房東家里有只鵝,很寶貝,就把鵝放到廚房自己的床底下。結(jié)果,第一天夜里就來(lái)了小偷,鵝被偷了。這小偷他媽的。50年后,回憶起這些時(shí)謝華安還是忍不住爆了句粗口。
在1990年代之前,很多個(gè)除夕夜謝華安都是在異鄉(xiāng)度過(guò)的。過(guò)年了,當(dāng)?shù)卮迕褡哂H訪友,謝華安和他的同事們就到田頭跟秧苗拜年,祈求來(lái)年豐收;再跟生產(chǎn)隊(duì)的牛拜年,祈求它們餓的時(shí)候,別踏進(jìn)田里吃稻子。
關(guān)于南繁,謝華安最喜歡講的一個(gè)故事是關(guān)于老鼠的,只要提起南繁,他都能再講一遍,而且每次都會(huì)有新的細(xì)節(jié)。水稻最怕的動(dòng)物是老鼠。牛吃了,水稻還有可能長(zhǎng)起來(lái);老鼠吃了,根就壞了,水稻也死了。在南繁,謝華安最頭疼的工作之一,就是斗老鼠。最初,他和同事們聚集在一起,通宵守著田地,趕老鼠。無(wú)果。秧田邊挖出深深的溝渠,老鼠也能成群游過(guò)去。找到薄膜圍住秧田,老鼠能跳到薄膜最高處,一躍而下,滿田亂竄。掛馬燈、稻草人、老鼠藥,什么辦法都試過(guò)。還有一奇招,頭戴礦燈,用蘆葦桿和鐵線自制弓箭,半夜間站在田埂邊射老鼠。我當(dāng)時(shí)心里都要笑死掉了,最現(xiàn)代的礦燈和最原始的弓箭去對(duì)付一只老鼠。
最后怎么解決這個(gè)老鼠問(wèn)題呢?
解決不了。
很多年里,謝華安像候鳥(niǎo)一樣,每年11月去海南,來(lái)年5月回福建。回福建的半年時(shí)間,他也幾乎都在試驗(yàn)田里。與謝華安有關(guān)的記憶,家人們能談起的不過(guò)都是水稻的故事。對(duì)他們來(lái)說(shuō),他是一個(gè)缺位的丈夫和父親。如今年紀(jì)大了,謝華安時(shí)常會(huì)和老同事們聊起往事,其中包括海南老房東家孩子們的童年趣事,但關(guān)于自家孩子的趣事,他一件也說(shuō)不出。妻子盧鳳英記得,幾個(gè)孩子小時(shí)候經(jīng)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去田里叫爸爸,但每次都是去了就回不來(lái)。派一個(gè),被留下,派兩個(gè),還是被留下,直到最后,她遠(yuǎn)遠(yuǎn)看著田里多了三個(gè)小不點(diǎn)兒。
真的想起來(lái)是很心酸的,謝華安回憶起這些的時(shí)候語(yǔ)氣也低沉起來(lái),我的孩子,樓上摔下來(lái),昏迷在醫(yī)院七天七夜,我也不在家。出車禍他媽的,腦袋都被打破掉,我也不在啊,都是我愛(ài)人。就她一個(gè)人撐在那個(gè)地方。半夜三更陪著孩子去醫(yī)院,第二天還上班。
妻子盧鳳英在向我回憶這些往事時(shí),她倒并不介懷,總是笑著,眼睛彎彎的。只有講到一件事情,她嚴(yán)肅起來(lái),臉上一直掛著的笑意也消失了。那是一件很小的事。有一年,她陪謝華安回南繁基地看望90多歲的老房東,老房東見(jiàn)到謝華安很高興,說(shuō):我的老謝又回來(lái)啦!她聽(tīng)到后立刻轉(zhuǎn)身對(duì)丈夫說(shuō):你現(xiàn)在變成房東的老謝了,不是我的老謝啦?
汕優(yōu)63團(tuán)隊(duì)成員 受訪者供圖
樂(lè)趣
與自然聯(lián)合創(chuàng)作,既需要直覺(jué)、品味和創(chuàng)造力,也意味著要比單打獨(dú)斗的天才們擁有更多的耐心。在選育種子的時(shí)候,謝華安經(jīng)常要從五六畝田里的數(shù)千株水稻中找到最好的那一個(gè)。用王烏齊——福建省農(nóng)科院的另一位水稻育種家的話說(shuō),他們是在尋找美人。經(jīng)過(guò)兩次雜交的水稻,有的像父本,有的像母本,有的既像父本又像母本。像父本的、像母本的,比父本和母本差的,都不能要,育種家需要的是比父母雙方都要更出色的個(gè)體。
數(shù)千株水稻怎么才能找出最好的那一株?
它好在哪里啊,這個(gè)是在人的感官里面,是一種直覺(jué),是一種在心里的感覺(jué)。一看就知道。謝華安說(shuō),當(dāng)然,這點(diǎn)眼光,不是一時(shí)得來(lái)的,是長(zhǎng)期積累,何況還要不斷地進(jìn)步。他會(huì)一遍,兩遍,很多遍地看,每天看,一株一株地看。只有數(shù)十年持續(xù)地觀察水稻,才能獲得潛移默化的,成為身體一部分的直覺(jué)和品味。
謝華安喜歡看水稻。尤其是水稻揚(yáng)花的時(shí)候,白嫩的小花——一朵花就是一粒谷子——飄蕩在綠色的田野中,美極了。女兒謝小丹很長(zhǎng)一段時(shí)間都不理解父親的行為。小時(shí)候,家門(mén)口就是一片稻田,吃飯的時(shí)候謝華安總是不和大家坐在一起,他自己端著碗坐在門(mén)口,一邊看著水稻一邊吃飯。謝小丹想,這稻田到底有什么好看的?
水稻育種最美妙和最痛苦的事情,都是等待。等待一株水稻長(zhǎng)大。從一粒種子開(kāi)始,抽出胚芽,長(zhǎng)成幼苗,秧苗入土后不斷拔節(jié),抽穗,開(kāi)花,結(jié)實(shí)。任何人都不能打擾這個(gè)節(jié)奏,不能加快,也不能減緩,只能讓它自己長(zhǎng)大。因此,謝華安們的工作周期是以年計(jì)的,觀察水稻的一次生命周期就是一年,即便是海南,一年也不過(guò)經(jīng)歷水稻的兩次生命周期。一個(gè)新的雜交水稻品種需要經(jīng)歷至少7次生命周期的觀察,才會(huì)有趨于穩(wěn)定的性狀表現(xiàn)。再加上種植試驗(yàn)和審定,一個(gè)雜交水稻品種,從培育到上市,一般需要8到10年的時(shí)間。
為了爭(zhēng)時(shí)間,謝華安有時(shí)會(huì)不惜成本。朱永生博士是福建省農(nóng)業(yè)科學(xué)院水稻研究所(以下簡(jiǎn)稱水稻所)的一位年輕科研人員,關(guān)于謝華安,他向我說(shuō)起一件印象深刻的事。2013年,謝華安聽(tīng)說(shuō)湖南有一個(gè)新品種檢測(cè)出抗東格魯病毒的基因,立刻讓人挖了一株正在開(kāi)花的稻子,放在裝著泥巴的塑料水桶中,坐著高鐵一路護(hù)送到南平,然后再讓司機(jī)把這株稻子接到沙縣的基地,交給他做雜交。如果你明年種下去,不是又要一年嗎?他就是搶那一年的時(shí)間。朱永生說(shuō),如果是他,很可能會(huì)讓對(duì)方寄點(diǎn)種子過(guò)來(lái),第二年種下去。
漫長(zhǎng)的工作周期使得很多育種學(xué)家到退休都培育不出一個(gè)好的品種,或者只有寥寥幾個(gè)拿得出手的品種——原因可能有很多,研究方向的偏離,機(jī)遇的錯(cuò)失,或者,只是缺少一些運(yùn)氣。畢竟,人生有幾個(gè)七八年呢?
謝華安是幸運(yùn)的那個(gè)。汕優(yōu)63不光成功了,而且創(chuàng)造了奇跡。根據(jù)過(guò)去的經(jīng)驗(yàn),一個(gè)成熟作物的抗病性會(huì)在5到6年內(nèi)發(fā)揮最佳優(yōu)勢(shì),時(shí)間到了,抗性逐漸衰退,病菌和蟲(chóng)子會(huì)在與作物的戰(zhàn)爭(zhēng)中收獲勝利。但是,汕優(yōu)63打破了這個(gè)規(guī)律,超出了科學(xué)家們的經(jīng)驗(yàn)范疇——汕優(yōu)63連續(xù)16年都頑強(qiáng)地生存,從未有過(guò)大規(guī)模的染病和減產(chǎn)。
沒(méi)人知道為什么。
謝華安承認(rèn)存在科學(xué)的偶然性。當(dāng)時(shí),有許多育種團(tuán)隊(duì)和謝華安選擇了相同的親本組合,但最終都沒(méi)有出成果。謝華安的成功當(dāng)然與他敏銳的意識(shí)到雜交水稻的出路在抗病,以及他對(duì)病毒圍攻的試驗(yàn)方式足夠堅(jiān)定有直接的關(guān)系,但另一方面,培育過(guò)程中的很多方面都不是他能夠控制的,人類只能等待大自然給出回應(yīng)。最終,大自然給了人類一個(gè)驚喜。
但作為與自然聯(lián)合創(chuàng)作的人類代表,謝華安卻從此背上了巨大的壓力。1990年,汕優(yōu)63在中國(guó)的推廣面積經(jīng)過(guò)四年迅速上升后達(dá)到頂峰。整個(gè)九十年代,每一個(gè)秋收的季節(jié),謝華安都會(huì)焦慮得睡不著覺(jué)。每一年都要等到9月中旬前后,沒(méi)有關(guān)于水稻得病和減產(chǎn)的警報(bào),才安心。
沒(méi)經(jīng)歷過(guò)的人不懂得,我當(dāng)時(shí)一個(gè)人能害怕到什么程度。謝華安擔(dān)憂的是,如此大的種植面積,覆蓋地區(qū)又如此之廣,如果發(fā)生病害,造成絕收,后果不堪設(shè)想。
你想對(duì)抗它,可又必須順應(yīng)它,永遠(yuǎn)不知道上天的心情。占志雄研究員是水稻所的書(shū)記,他的專業(yè)是植物保護(hù)——更具體一點(diǎn),他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和對(duì)付一群小蟲(chóng)子——他特別能夠理解謝華安的害怕。這些與大自然聯(lián)合創(chuàng)作的農(nóng)學(xué)家,對(duì)自然有著復(fù)雜的情感,他們敬畏自然,有時(shí)又想戰(zhàn)勝它,可是,戰(zhàn)勝之后呢,又不知道它的力量邊界在哪里,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打敗、被反噬了。
人類在自然面前,始終面臨的是巨大的未知、不確定和時(shí)刻發(fā)生的動(dòng)態(tài)變化。不過(guò),這固然有時(shí)讓人頭疼甚至害怕,但它也是農(nóng)業(yè)研究最迷人的地方。
占志雄舉了一個(gè)例子。他剛到福建省農(nóng)業(yè)科學(xué)院的時(shí)候,遇上稻癭蚊全省大爆發(fā),水稻減產(chǎn)70%。稻癭蚊是一種身長(zhǎng)不到5毫米的昆蟲(chóng),喜歡吸食水稻生長(zhǎng)點(diǎn)的汁液,導(dǎo)致水稻長(zhǎng)成蔥一樣的東西,不再抽穗結(jié)實(shí)。為了對(duì)付這只小蟲(chóng)子,占志雄在田間守了三個(gè)月,做了一輪又一輪的藥物篩選,引進(jìn)了很多專門(mén)防治稻癭蚊的藥物。到了第二年的發(fā)病季節(jié),所有應(yīng)對(duì)措施都準(zhǔn)備充分了,結(jié)果,稻癭蚊全體銷聲匿跡了,好像大自然召回了它們。后來(lái)這么多年稻癭蚊再也沒(méi)有爆發(fā)過(guò)。至于其中的原因,至今沒(méi)人說(shuō)得清。
能說(shuō)得清的只有一個(gè)基本的規(guī)律——昆蟲(chóng)總是跟人在斗爭(zhēng)中相互進(jìn)步。你發(fā)明了這個(gè)藥,對(duì)這個(gè)昆蟲(chóng)效果好,慢慢的它產(chǎn)生抗藥性,你又要去發(fā)明一種新的藥。占志雄還在北京農(nóng)業(yè)大學(xué)(中國(guó)農(nóng)業(yè)大學(xué)前身)讀書(shū)時(shí),一位植保專業(yè)的老教授和他說(shuō)過(guò)一句話,一輩子,一個(gè)人養(yǎng)一頭蟲(chóng)養(yǎng)不活,殺一頭蟲(chóng)殺不死,這就是我們植保的樂(lè)趣。
占志雄是個(gè)樂(lè)呵呵的農(nóng)學(xué)家,和他聊天總是有聽(tīng)不完的笑聲。在食堂里遇見(jiàn)他,他笑著說(shuō),要多吃一點(diǎn),水稻所的飯好吃的吧?在走廊遇見(jiàn)他,他的笑聲又能回蕩起來(lái),哎喲,你又來(lái)了!他好像總是快樂(lè)。他說(shuō)這是因?yàn)檫€有好多好多蟲(chóng)子沒(méi)有研究透,還有很多場(chǎng)與自然,與大地的搏斗沒(méi)有完成,與天斗其樂(lè)無(wú)窮,與蟲(chóng)斗其樂(lè)無(wú)窮,一輩子都在斗。如果都解決了,也就沒(méi)什么稀奇了。
但是,如果一輩子都斗不過(guò),會(huì)遺憾嗎?我問(wèn)他。他又大笑起來(lái),那多有意思呀。一輩子斗不過(guò),就一輩子干不完,那就一輩子快樂(lè)。
2010年,謝華安在南繁基地 受訪者供圖
把材料傳遞下去
采訪王烏齊的那天,他一直在抽煙。太久沒(méi)有和水稻專業(yè)之外的人打交道,他不那么放松。他說(shuō),我的故事不值一提。當(dāng)我問(wèn)他,他的材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東西嗎?他突然停下來(lái),掐滅了手里的煙,用很緩慢的語(yǔ)氣說(shuō),像我這個(gè)年紀(jì)什么都忘記掉,很多人的名字現(xiàn)在都忘記掉了。接著他把手搭在記載本上,俯身向前,像有什么小秘密要告訴我似的,自己的材料還好不會(huì)忘記掉。一個(gè)一個(gè)的名字都還有印象嘛。
王烏齊曾經(jīng)最擔(dān)心的,也是自己的材料找不到一個(gè)合適的人來(lái)把這些繼續(xù)做下去。他和我提起之前水稻所有位女同事,剛評(píng)上研究員,卻不幸因?yàn)檐嚨溡馔馊ナ溃牟牧弦簿瓦@樣被擱置了,很可惜。
這也是很多老一輩育種家們?cè)趹n心的一個(gè)問(wèn)題——能否找到合適的年輕人,把自己的經(jīng)驗(yàn)和材料傳遞下去。
一位育種家和我說(shuō),材料是除了家人以外最重要的東西。謝華安說(shuō),這輩子看過(guò)的材料都在他的腦海里,閉上眼睛像過(guò)電影一樣,每個(gè)品種的一生都會(huì)播放一遍。而王烏齊,把這些電影畫(huà)面記在了本子上,他有很多的記載本,他用鉛筆在上面寫(xiě)滿了每一個(gè)品種的數(shù)據(jù)、產(chǎn)量和形態(tài)變化。他經(jīng)手的水稻,都在記載本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。
他們都想過(guò)讓自己的孩子做這行,但孩子們絕大多數(shù)都是不愿意的。水稻所一位今年即將退休的研究員告訴我,他和妻子都在水稻所工作,但他們的孩子從小發(fā)誓,寧可讀中專也不讀農(nóng)學(xué)。
從畢業(yè)生中招人也越來(lái)越難。2019年進(jìn)入水稻所的一個(gè)研究人員告訴我,他的同學(xué)都不愿意來(lái)科研所,相比高校、種子公司,這里太清苦了。他記得,2019年,省農(nóng)科院開(kāi)放了28個(gè)崗位,最后報(bào)名去面試的只有12人。
關(guān)于水稻研究行業(yè)的清苦,占志雄講了一件趣事。有次水稻所的幾個(gè)博士和碩士在田里插秧,一個(gè)黎族阿姨帶著孩子路過(guò)。她停下來(lái)教育孩子,要好好讀書(shū)啊,不讀書(shū)以后跟叔叔一樣就在田里去種田。當(dāng)時(shí),幾個(gè)年輕人差點(diǎn)哭了,想跟孩子說(shuō),千萬(wàn)不要讀書(shū),以前不下田的,念完博士就下田了。
不過(guò),挺幸運(yùn)的是,王烏齊找到了一個(gè)年輕人來(lái)接手他的材料。現(xiàn)在年紀(jì)大,打算不做了,要交給小朱叫他做。他說(shuō)的小朱名叫朱永生,原本的專業(yè)是植物保護(hù),研究的是水稻上的一種真菌病原體,現(xiàn)在,他一邊繼續(xù)原本的研究——找尋水稻生病的原因,一邊接過(guò)王烏齊的材料,嘗試水稻抗病育種的研究。
其實(shí),很長(zhǎng)時(shí)間里,朱永生是厭惡水稻的。他出生在江西農(nóng)村,七八歲時(shí)開(kāi)始跟著父母犁田、插秧,天氣最炎熱的時(shí)候割稻子,從清晨四五點(diǎn)收到中午。小時(shí)候,他覺(jué)得水稻是一項(xiàng)人生任務(wù),非常害怕,非常討厭,總盼著什么時(shí)候擺脫它。命運(yùn)就是如此奇妙,他高考陰差陽(yáng)錯(cuò),被調(diào)劑進(jìn)了一所985大學(xué)的農(nóng)學(xué)專業(yè)。農(nóng)學(xué)實(shí)在不喜歡,又換成了植保專業(yè)。博士畢業(yè)后,他想過(guò)去農(nóng)藥公司,也有人推薦他去園林局,兜兜轉(zhuǎn)轉(zhuǎn),最終還是來(lái)到了水稻所。
到水稻所之后,漸漸的,他被所里的氛圍和人打動(dòng)了,尤其是王烏齊對(duì)水稻研究的熱情擊中了他。我和朱永生接觸的幾天里,在提到王烏齊的時(shí)候他是最激動(dòng),最有表達(dá)欲的。他反復(fù)在桌面上劃來(lái)劃去,向我描述王烏齊的記載本有多漂亮,還主動(dòng)幫我邀約從不接受采訪的王烏齊。他沒(méi)有退休生活,這個(gè)就是他最大的樂(lè)趣和愛(ài)好。癡迷啊,世界里好像沒(méi)有別的事。謝老師,王所長(zhǎng)他們這一代人確實(shí)是給我們留下了挺多的東西的。
袁隆平與謝華安在海南田頭 受訪者供圖
自然的答案
謝小丹曾經(jīng)是農(nóng)二代的例外。她學(xué)了農(nóng)學(xué),并且做了幾年育種。工作后,她陪父親去南繁的時(shí)候,遇到了很多國(guó)內(nèi)知名的育種家,他們看到謝華安身邊站著自己的女兒,都羨慕壞了。
但她最后也還是離開(kāi)了水稻育種。工作幾年后,她突然不想做水稻育種了。原因有很多,最重要的那個(gè)是因?yàn)樗辉傧氤蔀楦赣H的依附,她希望當(dāng)別人提起她的時(shí)候,首先說(shuō)的是謝小丹,而不是院長(zhǎng)的女兒。
她重新選擇了行業(yè)。這類的作物在水稻研究中都屬于雜草,起初,她看著總不太順眼,忍不住想拔掉。后來(lái)覺(jué)得也漂亮,四季都是美的。冬去春來(lái),鋪過(guò)保溫膜的田埂像一條條白龍,慢慢白龍身上冒出了一點(diǎn)綠色,等煙株越長(zhǎng)越大,漫野郁郁蔥蔥。即便到了冬天,田里什么都沒(méi)有,把秋天的稻桿翻滾進(jìn)去,也別有一番味道。
你說(shuō)它(大自然)每年都一樣嗎,它其實(shí)一樣,但是也都不一樣。從某種意義上講,她終究還是走上了父親的道路——曾經(jīng)對(duì)父親感到不解的她也像父親一樣可以從自然中發(fā)現(xiàn)美,找到快樂(lè)了,繁茂有繁茂的美,滄桑有滄桑的美。農(nóng)業(yè)跟大自然太近了,最大的樂(lè)趣就是這種動(dòng)態(tài)。
2020年,謝華安第一次在家待滿半年。因?yàn)橐咔椋荒茉贃|跑西跑了,40多年來(lái),謝小丹還從沒(méi)有和父親相處過(guò)這么長(zhǎng)的時(shí)間。她也得以少有的近距離觀察父親:父親的皮膚好像白了一點(diǎn),胃還是不太好,喜歡吃軟爛的食物。
但疫情稍微有所好轉(zhuǎn),謝華安又迫不及待地往試驗(yàn)區(qū)跑了。這些年,他的心思轉(zhuǎn)到了超級(jí)稻和功能稻品種的研究上。超級(jí)稻是在豐產(chǎn)、優(yōu)質(zhì)、抗性和廣適應(yīng)性四個(gè)方面取最大公約數(shù)——簡(jiǎn)單地說(shuō),不只要產(chǎn)量高、抗病害,還要口感好、品質(zhì)高;功能稻則是針對(duì)特定病人的水稻品種,比如有的針對(duì)糖尿病人,有的針對(duì)腎臟病人。
似乎什么時(shí)候都不能松一口氣。汕優(yōu)63之后,謝華安培育的水稻品種又有多個(gè)創(chuàng)下產(chǎn)量世界紀(jì)錄,但他仍然有很多操心的事情,從水稻、中國(guó)人的吃飯問(wèn)題到人與自然的關(guān)系——
我們?nèi)祟惒灰鲜窍朊暌曌匀唬詈蠛Φ氖亲约骸,F(xiàn)在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大肆地掠奪自然,人類為了滿足現(xiàn)在這一代人的需求,過(guò)奢侈的生活,可是我們后代的生存都會(huì)成問(wèn)題的,很多人還看不到。他舉了一個(gè)例子,我們從超市買(mǎi)的餅干,一塊小小的餅干,里面一個(gè)塑料小盤(pán)子,外面還要再加一層塑料,你吃一塊餅干,這兩塊塑料,七八年了大自然還消化不了它,我們?nèi)司褪沁@樣破壞(自然)的,真的是作死,你干嘛要這樣子啊?
我問(wèn)謝華安,他是怎么看待他和水稻的關(guān)系的?謝華安和我說(shuō),水稻對(duì)他來(lái)說(shuō)不止是一種作物,很多時(shí)候更是他的一種寄托,一種精神上的伙伴。60多年的水稻研究,他明白了一點(diǎn)——人類和水稻一樣,都是自然進(jìn)化的產(chǎn)物;人類想要活,水稻也想要,培育水稻的過(guò)程是科學(xué)家們和水稻共同找到一個(gè)生存之道。
我們談起這些的時(shí)候,身旁有十幾個(gè)農(nóng)民在收稻谷,遠(yuǎn)處是廣袤的青綠色芋田和青山。謝華安在左手手心捻了捻剛吸完的煙,指著水田邊的一棵野草和幾顆田螺,繼續(xù)說(shuō):野草、果實(shí)、昆蟲(chóng)、水稻這些物種都和人類一樣,是與大自然適應(yīng)的結(jié)果。我們永遠(yuǎn)不知道自然的答案。只要站在大地上,就會(huì)有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水稻所試驗(yàn)田 攝影 | 賴祐萱
(感謝福建省農(nóng)業(yè)科學(xué)院水稻研究所張建福、鄭家團(tuán)、楊惠杰、涂詩(shī)航、蔡秋華、林強(qiáng)、肖晏嘉對(duì)本文采訪提供的幫助。)